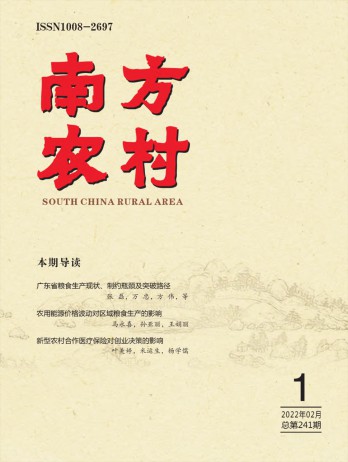首頁(yè) > 精品范文 > 農(nóng)村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
農(nóng)村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精品(七篇)
時(shí)間:2023-10-11 16:14:25
序論:寫(xiě)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(dá)。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,挖掘那些隱藏在內(nèi)心深處的真相,好投稿為您帶來(lái)了七篇農(nóng)村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范文,愿它們成為您寫(xiě)作過(guò)程中的靈感催化劑,助力您的創(chuàng)作。

篇(1)
無(wú)獨(dú)有偶,學(xué)術(shù)界最近舉行的“社會(huì)文化變革與中國(guó)當(dāng)代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的發(fā)展”研討會(huì),也提出一個(gè)看似危言聳聽(tīng)的話題,即“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會(huì)不會(huì)消失”?這個(gè)議題非杞人憂天,它體現(xiàn)了知識(shí)分子的憂患意識(shí)和前瞻性,以美國(guó)文學(xué)為例,自福克納之后,歷史鄉(xiāng)土小說(shuō)基本就很少見(jiàn)到了。
當(dāng)城市化一步步挺進(jìn)鄉(xiāng)土中國(guó)時(shí),這些隱憂也一步步呈現(xiàn)到我們面前,總有一天,會(huì)變得迫在眉睫。現(xiàn)在,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篇《情歸何處》,已然透露出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在逐漸蛻化過(guò)程中的突圍方向,那就是從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走向都市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。
做出這樣的判斷,需要我們回到文學(xué)史的脈絡(luò)進(jìn)行梳理。
“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”最早由魯迅在《新文學(xué)大系?小說(shuō)二集導(dǎo)言》中提出,他說(shuō):“蹇先艾敘述過(guò)貴州,裴文中關(guān)心著榆關(guān),凡在北京用筆寫(xiě)出他的胸臆來(lái)的人們,無(wú)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,其實(shí)往往是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,從北京這方面說(shuō),則是僑寓文學(xué)的作者。”根據(jù)這一描述,并結(jié)合魯迅、許杰、臺(tái)靜農(nóng)、廢名、以至后來(lái)的沈從文和汪曾祺等人的作品,我們可以發(fā)現(xiàn),在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中,鄉(xiāng)土中國(guó)成為作家批判或者謳歌的對(duì)象。如20年代許杰、臺(tái)靜農(nóng)、蹇先艾等作家,基本繼承了魯迅改造國(guó)民性的思想,對(duì)落后的農(nóng)村多批判而少欣賞;與此不同的是廢名,他對(duì)鄉(xiāng)土則懷著詩(shī)意般的美好記憶,此后沈從文、汪曾祺也是如此。不過(guò),無(wú)情的批判也好,美好的緬懷也罷,他們的文學(xué)世界中始終存在一個(gè)鄉(xiāng)村世界,如沈從文的湘西、汪曾祺的高郵、蹇先艾的貴州等。
《情歸何處》這篇小說(shuō)的作者卞正鋒,正如20年代的鄉(xiāng)土派作家一樣,也是來(lái)自鄉(xiāng)村,懷著夢(mèng)想來(lái)到大城市。在上海的當(dāng)下,像卞正鋒這樣的作家不在少數(shù),他們的處境和80年前左右的鄉(xiāng)土派青年作家很是相似,他們的創(chuàng)作無(wú)法離開(kāi)鄉(xiāng)村經(jīng)驗(yàn),但是,他們對(duì)鄉(xiāng)村經(jīng)驗(yàn)的敘事大大的不同于20年代的鄉(xiāng)土派作家。一個(gè)顯然的區(qū)別在于他們的鄉(xiāng)土敘事帶有漠視和驅(qū)逐鄉(xiāng)土的情感元素。為了說(shuō)明這一點(diǎn),可以做個(gè)比較。《水葬》是蹇先艾的成名作,它向我們展示了古老鄉(xiāng)村用天經(jīng)地義的心態(tài)去水葬一位有偷竊行為的青年,以及在此儀式中群眾對(duì)生命的麻木和殘忍。小說(shuō)強(qiáng)烈地流露出魯迅式的批判庸眾情懷。鄉(xiāng)土中國(guó)雖然在他的敘事中成為了豪無(wú)詩(shī)意且急需變革的地方,但是,他對(duì)鄉(xiāng)土的情感是熾熱的,惟其如此,才會(huì)承續(xù)改造國(guó)民性的思想。蹇先艾他們那批鄉(xiāng)土派作家,始終直面鄉(xiāng)村經(jīng)驗(yàn),鄉(xiāng)土中國(guó)成為他們作品中不可回避的世界。
在小說(shuō)《情歸何處》中,這種情感發(fā)生了質(zhì)的變化,小說(shuō)女主角梅子來(lái)自鄉(xiāng)村,在上海艱難地生存著,希望通過(guò)奮斗或者嫁個(gè)上海老公,日子能夠逐漸好起來(lái)。在這篇小說(shuō)中,鄉(xiāng)土空間已經(jīng)消失,不過(guò),鄉(xiāng)土元素還是壓縮在梅子的內(nèi)心世界中,我們能夠從梅子身上的一些品質(zhì)(如面對(duì)高峰質(zhì)樸的愛(ài)情,洗頭房中無(wú)奈而倔強(qiáng)的反抗等),找到某種鄉(xiāng)土期待。但是,如果對(duì)這篇小說(shuō)的情感進(jìn)行粗疏的概括,它與傳統(tǒng)鄉(xiāng)土派的文學(xué)的區(qū)別是明顯的,從精神層面來(lái)看,鄉(xiāng)土世界已經(jīng)不再是鄉(xiāng)下人進(jìn)城敘事中無(wú)法繞開(kāi)的表現(xiàn)對(duì)象。在城市化進(jìn)程下,鄉(xiāng)村被判定為一個(gè)落后的、必然被征服和淘汰的角色。對(duì)于這樣一個(gè)充滿否定化描述的空間,已經(jīng)很難承擔(dān)起精神家園的重?fù)?dān)。它不可能像沈從文的鄉(xiāng)土世界,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;也不能像蹇先艾筆下的鄉(xiāng)土世界,牽著作家一顆外冷內(nèi)熱的批判之心。而《情歸何處》中的鄉(xiāng)土世界,是梅子千方百計(jì)想要驅(qū)逐、想要離開(kāi)的地方。在精神層面上,鄉(xiāng)土世界已經(jīng)被放逐了,因?yàn)樗辉儆心芰Τ袚?dān)精神價(jià)值,即使是批判性的。所以,在類似《情歸何處》這樣的作品中,鄉(xiāng)土空間基本消失了,即使偶爾出現(xiàn),也只是一個(gè)空殼。
篇(2)
臉皮厚吃個(gè)夠下一句是針都扎不透。“皮薄吃不著,臉皮厚吃個(gè)夠”指人做事太顧顏面,什么也撈不到;只有不顧羞恥,才能得利。出處是劉紹棠《十步香草》三七:“燕菱,臉皮薄吃不著,臉皮厚吃個(gè)夠,我這一雙眼可開(kāi)了葷。長(zhǎng)舌婦楊桂子最能沒(méi)縫下蛆,造謠行事。”
劉紹棠(1936年2月29日~1997年3月12日),中國(guó)著名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作家,“荷花淀派”的代表作家之一,“大運(yùn)河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體系”創(chuàng)立者。13歲時(shí)就開(kāi)始發(fā)表作品,加入作協(xié)時(shí)是當(dāng)時(shí)最年輕的作協(xié)會(huì)員。受到作家孫犁和肖洛霍夫的影響,走上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之路,作品題材多以京東運(yùn)河(北運(yùn)河)一帶農(nóng)村生活為題材,格調(diào)清新淳樸,鄉(xiāng)土色彩濃郁。他的作品曾多次獲國(guó)內(nèi)獎(jiǎng)項(xiàng)并受國(guó)家嘉獎(jiǎng);又有多部作品被翻譯成外文,在國(guó)際上亦有所影響。
(來(lái)源:文章屋網(wǎng) )
篇(3)
城市文學(xué)經(jīng)驗(yàn)相對(duì)匱乏,是挑戰(zhàn)也是空間
談?wù)摮鞘信c文學(xué),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自然成為一個(gè)繞不過(guò)去的參照,實(shí)際上,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表現(xiàn)城市生活的諸多欠缺,正是在與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的比較當(dāng)中形成的。與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傳統(tǒng)深厚、作家眾多、優(yōu)秀作品不斷呈現(xiàn)的成就相比,中國(guó)現(xiàn)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缺乏優(yōu)秀的城市文學(xué)可謂是文學(xué)界的共識(shí),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與城市發(fā)展的距離引起關(guān)注。
“中國(guó)文學(xué)的鄉(xiāng)土傳統(tǒng)太強(qiáng)大了,那么城市在中國(guó)文學(xué)中應(yīng)是一種何種形象和何種地位呢?這是我們編輯部一直在關(guān)切的問(wèn)題。”作家劉醒龍雖然也是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作家中的重要一員,但是作為文學(xué)刊物的主編,他也明顯感覺(jué)到了整體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上的這種不平衡,為此,他所在的《芳草》雜志于今年8月初在武漢舉辦了“城市的文學(xué)形象研討會(huì)”。
評(píng)論家汪政介紹說(shuō):“從去年到今年不到一年的時(shí)間里,就我本人而言已經(jīng)參加這樣相同主題的研討會(huì)四個(gè),南京、廣東、上海、武漢,提的都是城市的文學(xué)。”由此可見(jiàn)現(xiàn)在城市與文學(xué)關(guān)系的緊迫和社會(huì)的普遍重視程度。汪政認(rèn)為,中國(guó)小說(shuō)傳統(tǒng)的源頭并不在鄉(xiāng)村,反而是市井,因?yàn)橹袊?guó)特殊的發(fā)展歷程,才使得鄉(xiāng)村和城市的關(guān)系變得錯(cuò)綜復(fù)雜。實(shí)際上,文學(xué)應(yīng)該參與到城市生活的建構(gòu)當(dāng)中,所以才會(huì)有巴爾扎克與巴黎、狄更斯與倫敦、老舍與北京、陸文夫與蘇州等重要的文學(xué)關(guān)系。但是,我們的城市至今沒(méi)能發(fā)展起豐沛的文學(xué)經(jīng)驗(yàn),無(wú)論是張愛(ài)玲還是老舍,這些有限的文學(xué)經(jīng)驗(yàn)都不足以涵括當(dāng)下的中國(guó)城市生活,作家必須要認(rèn)真思考如何為中國(guó)文學(xué)提供獨(dú)特的城市文學(xué)經(jīng)驗(yàn)以及中國(guó)城市文學(xué)的未來(lái)。
“在中國(guó)的文學(xué)傳統(tǒng)中,特別是中國(guó)現(xiàn)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傳統(tǒng)中,農(nóng)村題材的創(chuàng)作具有很大的優(yōu)勢(shì),這種優(yōu)勢(shì)體現(xiàn)在很多地方,比如說(shuō)創(chuàng)作實(shí)力雄厚,能夠在各個(gè)層面上獲得認(rèn)可的作家,絕大多數(shù)都是從事農(nóng)村題材的創(chuàng)作。甚至可以說(shuō),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近百年的發(fā)展格局造就了一種農(nóng)村題材占據(jù)道德優(yōu)勢(shì)的局面,這和我們的社會(huì)發(fā)展有關(guān),和我們長(zhǎng)期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的生活經(jīng)驗(yàn)有關(guān),但今天來(lái)看,和我們的文學(xué)觀念、價(jià)值評(píng)判標(biāo)準(zhǔn)也有關(guān)系。”評(píng)論家們認(rèn)為,中國(guó)的城市文學(xué)剛剛起步,很多基礎(chǔ)性、理論性的問(wèn)題需要解決。
文學(xué)不應(yīng)“憎恨”城市
“我們的小說(shuō)敘事充滿了對(duì)城市的傲慢感,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狹隘地、怨恨地對(duì)待城市”,評(píng)論家李建軍認(rèn)為,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因?yàn)閺?fù)雜的社會(huì)原因所形成的對(duì)待城市的消極態(tài)度損害了對(duì)城市生活的真實(shí)表達(dá)和深刻思考。
李建軍認(rèn)為,現(xiàn)代意義上的城市是開(kāi)放的、利于交往的、公平的,是人類新的文化空間,我們的作家不應(yīng)該過(guò)分強(qiáng)調(diào)鄉(xiāng)村和城市之間的壁壘,而應(yīng)該站到人類生存空間的高度進(jìn)行文學(xué)書(shū)寫(xiě),即便寫(xiě)的是一個(gè)狹小的地域的故事,寫(xiě)的是某一種生活,但是有面對(duì)全人類的內(nèi)心世界敘說(shuō)的格調(diào)。他舉例說(shuō),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等偉大的作家都沒(méi)有這種狹隘的地域和生活方式的區(qū)分,他們面對(duì)的是整個(gè)人類的心靈空間。表現(xiàn)人的現(xiàn)代性,體現(xiàn)人的價(jià)值和尊嚴(yán),營(yíng)造包容和開(kāi)放的文化空間,這才是城市文學(xué)應(yīng)有的高度。
與會(huì)者也提出,我們應(yīng)當(dāng)深思文學(xué)對(duì)待城市的態(tài)度。很多小說(shuō),尤其是“鄉(xiāng)下人進(jìn)城”模式的小說(shuō),往往都強(qiáng)調(diào)農(nóng)民在城市受到的屈辱、冷漠以及對(duì)城市的憎恨等等,大家會(huì)認(rèn)為這是來(lái)自底層的、正義的、有良知的聲音。但是我們反過(guò)來(lái)想一下,假如說(shuō)一個(gè)寫(xiě)城市題材的作家如果表達(dá)了對(duì)農(nóng)村的不滿和憎恨,很可能他的價(jià)值觀就會(huì)受到非常廣泛的質(zhì)疑。雖然城市文學(xué)的寫(xiě)作目前不可避免地帶有欲望化寫(xiě)作、類型化寫(xiě)作、發(fā)泄式寫(xiě)作的缺失,但并不意味著城市就只能成為道義上的批判對(duì)象和文學(xué)上的附庸,而應(yīng)該更積極地尋求深遠(yuǎn)的表達(dá)。
作家魏天無(wú)認(rèn)為,作家一方面要深入到城市生活去,另一方面也應(yīng)該有超越的眼光和胸襟,同時(shí)要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一刻謙遜的心態(tài),如果作家只是在作品中一味地追逐時(shí)尚的生活方式和話語(yǔ)方式,那么他的創(chuàng)作是沒(méi)有生命力的。反過(guò)來(lái)說(shuō),如果作家總是保持一種懷疑一切、否定一切的消極心態(tài),那他筆下的形象要么是殘缺的,要么是缺乏溫度的。城市文學(xué)應(yīng)該展現(xiàn)生活的理想之道,能夠容納并善待每一個(gè)生靈,能夠讓人們從容地面對(duì)自己和他人。
避免“運(yùn)動(dòng)化”和“幸福化”
面對(duì)各種方式的“城市文學(xué)”呼聲,以及各地方打造城市“文學(xué)名片”的文化建設(shè)工程,很多評(píng)論家也提醒,要尊重文學(xué)自身的規(guī)律,不應(yīng)為趕潮流而浮皮潦草地或美化式地書(shū)寫(xiě)城市,要深入到現(xiàn)代城市生活的眾生百態(tài)和文化肌理中去思考人的生存和心靈圖景。
“我們要認(rèn)真研究城市文學(xué)的問(wèn)題,但是我們也沒(méi)有必要太焦慮,要尊重文學(xué)本身的規(guī)律,不能轉(zhuǎn)身又去‘組織’書(shū)寫(xiě)城市”,評(píng)論家吳義勤認(rèn)為,就中國(guó)現(xiàn)在的文學(xué)經(jīng)驗(yàn)和生活經(jīng)驗(yàn)來(lái)說(shuō),人們更樂(lè)于接受鄉(xiāng)村文學(xué)有其必然性,因?yàn)槌鞘凶鳛橐粋€(gè)現(xiàn)代的產(chǎn)物在中國(guó)的建構(gòu)是滯后的,城市經(jīng)驗(yàn)的產(chǎn)生和積累也是滯后的,如果城市的審美想象沒(méi)有完成的時(shí)候,不太可能產(chǎn)生很好的城市文學(xué),我們的審美經(jīng)驗(yàn),可能不足以支撐一個(gè)轟轟烈烈的文學(xué)上的“城市運(yùn)動(dòng)”。
“我們現(xiàn)在很多的中國(guó)形象、地區(qū)形象、城市形象理論很熱,但是我們?cè)谟懻撨@個(gè)形象的問(wèn)題時(shí),容易產(chǎn)生一種迷失,其實(shí)要警惕的就是我們往往很難意識(shí)這個(gè)問(wèn)題,是文學(xué)的問(wèn)題,最根本的問(wèn)題我覺(jué)得還是寫(xiě)人,所以我覺(jué)得書(shū)寫(xiě)或者說(shuō)討論這個(gè)問(wèn)題,更重要的是要超越這個(gè)問(wèn)題,要達(dá)到人類和人的問(wèn)題上。”評(píng)論家何言宏認(rèn)為不要無(wú)論寫(xiě)何種題材,文學(xué)內(nèi)部的基本要素都不能被減弱。
作家馬步升認(rèn)為,很多城市包括很小的城市都在打自己的文化品牌,這是一個(gè)現(xiàn)代化熱潮中的特殊現(xiàn)象,它的根源是一種文化身份的焦慮感,現(xiàn)代化和城市化一方面走在“趨同”之路上,一方面又力求不同之處,文學(xué)究竟要在其中承擔(dān)什么樣的功能是值得深思的。
篇(4)
【關(guān)鍵詞】《祝福》;《荷花淀》;藝術(shù)風(fēng)格
在上世紀(jì)20年代,魯迅開(kāi)創(chuàng)了鄉(xiāng)土小說(shuō)流派,成為了描寫(xiě)農(nóng)村與農(nóng)民的第一人,尤其是對(duì)于農(nóng)村婦女的描寫(xiě)更是對(duì)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的創(chuàng)新。到了40年代,孫犁的小說(shuō)也在社會(huì)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,被親切的成為“荷花淀派”創(chuàng)始人。
魯迅的代表作《祝福》與孫犁的代表作《荷花淀》都是描寫(xiě)中國(guó)農(nóng)村與農(nóng)民的作品,深刻的反應(yīng)了當(dāng)時(shí)的歷史狀態(tài),刻畫(huà)出了兩個(gè)豐滿的農(nóng)村婦女形象,下面就針對(duì)這兩種藝術(shù)風(fēng)格進(jìn)行深入的對(duì)比。
一、人物內(nèi)心世界的塑造
任何小說(shuō)都是要將人物形象的塑造作為核心的,如果可以塑造出一位形象生動(dòng)的人物,那么小說(shuō)就成功了一半,想要塑造出經(jīng)典作品,就需要充分的審視人物的靈魂。
一直以來(lái),魯迅都十分注意白描手法的使用,白描本身是國(guó)畫(huà)的一種創(chuàng)作手法,有著明快、簡(jiǎn)練以及質(zhì)樸的特征,可以用簡(jiǎn)單的線條來(lái)勾勒出震懾人心的畫(huà)面。將白描應(yīng)用在文學(xué)作品就是指使用精煉的筆法來(lái)表現(xiàn)事件與人物的一種方法。
魯迅小說(shuō)的語(yǔ)言都十分的樸實(shí),但是這些樸實(shí)的語(yǔ)言中蘊(yùn)含這極為豐富的思想。例如,在《祝福》中,魯迅描寫(xiě)到,“我”在第一次看到祥林嫂時(shí),“五年前花白的頭發(fā)即今已經(jīng)全白,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”;“臉上削瘦不堪,黃中帶黑,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顏色”。
對(duì)祥林嫂外貌的描寫(xiě)方式是通俗普通的,但是通過(guò)作者的描寫(xiě),我們可以看到一個(gè)受舊社會(huì)壓迫的農(nóng)村婦女形象,她生活窘迫,精神困苦不堪,通過(guò)這簡(jiǎn)短的語(yǔ)言充分的描述出了當(dāng)時(shí)農(nóng)民的生活狀態(tài)。
孫犁極大的受到魯迅創(chuàng)作風(fēng)格的影響,十分推崇白描的手法,在《荷花淀》中也應(yīng)用了大量的白描手法,與《祝福》相比而言,孫犁主要借助人物的行動(dòng)與語(yǔ)言來(lái)表情達(dá)意,對(duì)話簡(jiǎn)練,極具個(gè)性。
例如,在聽(tīng)說(shuō)丈夫報(bào)名地區(qū)隊(duì)之后,水生嫂低下頭說(shuō)道:
“你總是很積極的。”;“你走,我不攔你,家里怎么辦?”
在這種簡(jiǎn)單的對(duì)話里可以看出水生嫂內(nèi)心的復(fù)雜情感,他知道丈夫干的事情很光榮,但是充滿了擔(dān)心。最后她帶領(lǐng)伙伴成立了隊(duì)伍,沖出敵人的包圍,為奉獻(xiàn)出了自己的力量。水生嫂是新時(shí)代女性的代表,她們不再逆來(lái)順受,有著不屈不饒的斗爭(zhēng)精神。
二、環(huán)境與性格命運(yùn)的關(guān)系
環(huán)境決定命運(yùn),祥林嫂與水生嫂的命運(yùn)都與環(huán)境僅僅的相連。魯迅的小說(shuō)反映出失敗到這一階段的社會(huì)變化,其創(chuàng)作的背景多集中在浙江東部城鎮(zhèn)與農(nóng)村,深刻的反映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下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的生活。
《祝福》描述出來(lái)的不僅僅是一副鄉(xiāng)村生活畫(huà)卷,在這幅祥和的畫(huà)卷中,也隱藏著深刻的矛盾,祥林嫂在祝福聲中走完了自己悲慘的人生,而活著的人們更多的是將熱情放在祭祀上,這就更加深刻的體現(xiàn)出封建社會(huì)人吃人的慘狀。
孫犁的小說(shuō)更加注重自然景物的描寫(xiě),這在孫犁的小說(shuō)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,這些自然景物不僅對(duì)于烘托氣氛,營(yíng)造環(huán)境有著十分重要的突出作用,與故事情節(jié)和人物心理的發(fā)展也相得益彰,互為襯托。
在《荷花淀》的開(kāi)頭,作者為我們展示出了這樣一幅恬靜的畫(huà)面:干凈涼爽的院子、初升的月亮、潮潤(rùn)潤(rùn)的葦眉子,院子中編席子的女人、水面的薄霧、帶著荷花香的微風(fēng)……
這種恬靜的畫(huà)面與水生嫂的內(nèi)心世界形成了和諧的對(duì)照,在人物心理的變化下,周圍的景物也發(fā)生了相應(yīng)的變化。在探夫途中遭遇襲擊時(shí),“一望無(wú)際密密層層的大荷葉迎著陽(yáng)光舒展開(kāi)來(lái),就像銅墻鐵壁一樣……”,此時(shí)的荷花淀成為了她們的庇護(hù)所,這不僅與人物的情感與行為相協(xié)調(diào),也有著強(qiáng)烈的象征意義。
三、篇幅與容量的對(duì)比
魯迅的小說(shuō)在簡(jiǎn)短的篇幅中常常可以提現(xiàn)出深刻的內(nèi)涵,這主要?dú)w功于作者豐富的人生閱歷以及敏銳的觀察力。
在《祝福》中,作者應(yīng)用了傳統(tǒng)小說(shuō)結(jié)構(gòu)表現(xiàn)方式,使用敘述加場(chǎng)景的描寫(xiě)方式,作品跨越時(shí)間長(zhǎng),但是截取了其中的典型畫(huà)面,通過(guò)簡(jiǎn)短的生態(tài)描寫(xiě)展示出了深刻的社會(huì)內(nèi)容,不僅凝聚者祥林嫂的艱辛,也埋藏著作者對(duì)于這些社會(huì)的控訴。
在篇幅與容量上,孫犁與魯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,在《荷花淀》中,并沒(méi)有用華麗的語(yǔ)言來(lái)描繪戲劇沖突與戰(zhàn)爭(zhēng)生活,而是從荷花淀這一背景上勾畫(huà)出富有情調(diào)與韻味的生活,從側(cè)面歌頌了農(nóng)村婦女的英勇才智。
總而言之,在魯迅與孫犁的作品中,都可以看到農(nóng)村與農(nóng)民的縮影,他們的創(chuàng)作方式不同,但是又有著一些相似之處,深入分析兩者的藝術(shù)風(fēng)格對(duì)于充實(shí)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的內(nèi)涵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。
參考文獻(xiàn):
[1]何以剛.真實(shí)地再現(xiàn)典型環(huán)境中的典型人物――魯迅小說(shuō)研究之一[J].廣西民族學(xué)院學(xué)報(bào)(哲學(xué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版),1980(02)
篇(5)
關(guān)鍵詞: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 心理沖突 流派沖突 性別沖突 城鄉(xiāng)沖突
一、不同流派作家之間的相互沖突
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史上的流派眾多,自晚清以降,活躍于文壇的有鴛鴦蝴蝶派、革命派、新感覺(jué)派、京派、《七月》派、解放區(qū)文學(xué)等主要派別,這些流派各自組織自己的社團(tuán)作為活動(dòng)的陣地,以宣傳自己的文學(xué)主張,呈現(xiàn)出鮮明的文學(xué)風(fēng)格。
其中,引起文壇關(guān)注的首先要數(shù)以周作人、鄭振鐸、沈雁冰、王統(tǒng)照、許地山、葉紹鈞等人為代表的文學(xué)研究會(huì)成員作家與以郭沫若、張資平、郁達(dá)夫、成仿吾、穆木天等人為代表的創(chuàng)造社成員之間的論爭(zhēng),前者注重文學(xué)的社會(huì)功用,被看作是“為人生而藝術(shù)”的一派,或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的一派,后者主張“為藝術(shù)而藝術(shù)”,強(qiáng)調(diào)文學(xué)必須忠實(shí)地表現(xiàn)作者自己內(nèi)心的需求,比較重視文學(xué)的美感作用,被看做是浪漫主義的一派。發(fā)展到后來(lái),以“左翼”文學(xué)為創(chuàng)作標(biāo)準(zhǔn)的一派作家主張文學(xué)應(yīng)當(dāng)為革命服務(wù),于是出現(xiàn)了以蔣光慈的《咆哮了的土地》為代表的革命主義文學(xué)。相比較而言,以沈從文、梁實(shí)秋、朱光潛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文學(xué)在言論中公公公開(kāi)反對(duì)“為藝術(shù)而藝術(shù)”,例如沈從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給那些“對(duì)中國(guó)社會(huì)變動(dòng)有所關(guān)心”、“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(fù)興大業(yè)的人”以“一種勇氣同信心”,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會(huì)人生,探求民族復(fù)興的道路,在動(dòng)蕩轉(zhuǎn)換的30年代,盡管自由主義知識(shí)分子處于嚴(yán)重的精神危機(jī)之中,但這一時(shí)期他們的文學(xué)主張卻很少受到西方世紀(jì)末文學(xué)的影響,較少頹廢、享樂(lè)的色彩,而顯示出某種嚴(yán)肅性:嚴(yán)肅地自我內(nèi)省,嚴(yán)肅地表現(xiàn)、思考社會(huì)人生。
二、不同性別作家之間的風(fēng)格差異
在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發(fā)展過(guò)程中,逐漸的有更多的女作家開(kāi)始從事于寫(xiě)作這一行業(yè),一改中國(guó)自古以來(lái)男作家?guī)缀踅y(tǒng)攝整個(gè)文壇的尷尬局面。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史上有名的女作家,起訖于陳衡哲、冰心、廬隱、凌叔華、石評(píng)梅等女作家,發(fā)展于蕭紅、丁玲、張愛(ài)玲、林徽因、楊絳等為更多讀者所知的女作家。女子開(kāi)始走出閨門(mén),介入社會(huì)公共生活,女性作家將女子獲得解放的權(quán)利進(jìn)行充分利用,將自身所體驗(yàn)到的日常生活、社會(huì)環(huán)境所賦予的孤獨(dú)與憂傷、寂寞與惆悵、困惑與迷茫,均通過(guò)審美沉思轉(zhuǎn)換為情感基調(diào)。其中,以張愛(ài)玲的作品最為廣大人知曉。張愛(ài)玲注重描寫(xiě)大時(shí)代下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,其眼光之毒辣,見(jiàn)解之大膽深刻,后無(wú)來(lái)者,為女性作家的創(chuàng)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筆。當(dāng)然,女作家的成就并沒(méi)有超越于男作家,在文學(xué)工作領(lǐng)域,男性作家還是相對(duì)而言處于有利地位,并產(chǎn)生了不可多得的大師級(jí)人物。首當(dāng)推崇的當(dāng)然是魯迅以及他的創(chuàng)作,除此之外,沈從文、巴金、老舍、等作家也為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男性作家的書(shū)寫(xiě)畫(huà)上了堅(jiān)實(shí)的一筆。男女作家同時(shí)積極的進(jìn)行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,這在中國(guó)文學(xué)史上是開(kāi)創(chuàng)性的一次嘗試,獲得自由書(shū)寫(xiě)權(quán)利的女作家,無(wú)比珍惜這個(gè)機(jī)會(huì),她們無(wú)不對(duì)女性曾經(jīng)歷以及現(xiàn)在經(jīng)歷的悲慘命運(yùn)進(jìn)行控訴,希望在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為女性爭(zhēng)得與男性一樣寬廣的生存空間。女性作家對(duì)自身權(quán)利的爭(zhēng)取自然會(huì)在許多方面與男性作家發(fā)生沖突,因此,男女作家之間爭(zhēng)奪話語(yǔ)權(quán)的戰(zhàn)爭(zhēng)自此拉開(kāi)帷幕。
三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碰撞
作家的生平背景是決定其日后創(chuàng)作風(fēng)格的重要影響因素,在現(xiàn)代作家群中,有些作家熱衷于書(shū)寫(xiě)對(duì)故鄉(xiāng)鄉(xiāng)土的懷戀,有些作家熱衷于書(shū)寫(xiě)對(duì)城市發(fā)展中所存在問(wèn)題的擔(dān)憂對(duì)于無(wú)奈,于是,兩種文學(xué)類型便由此而形成。其中,最先于魯迅作品《孔乙己》、《風(fēng)波》、《故鄉(xiāng)》、《祝福》中展現(xiàn)出的對(duì)鄉(xiāng)下農(nóng)村的懷戀之情,自此開(kāi)啟了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的創(chuàng)作傳承,為后來(lái)的鄉(xiāng)土作家建立了規(guī)范。一般而言,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作家們靠回憶重組來(lái)描寫(xiě)故鄉(xiāng)農(nóng)村的生活,帶有著濃重的鄉(xiāng)土氣息和地方色彩。1923年后,一批以文學(xué)研究會(huì)的知識(shí)分子為主的青年作者,便帶著他們極具濃厚鄉(xiāng)土氣息的小說(shuō)作品,紛紛登上文壇,形成了鄉(xiāng)土小說(shuō)的第一個(gè)。處于這一中而成就較為顯著的是王魯彥、彭家煌、臺(tái)靜農(nóng)等人。代表作品有王魯彥的《柚子》、《菊英的出嫁》,彭家煌的《慫恿》,臺(tái)靜農(nóng)的《地之子》等等。
而在另外一方面,生活與城市之中的作家,尤其是生活的于市井之內(nèi)的作家,如張愛(ài)玲、老舍、巴金、茅盾之類,其作品大多數(shù)表現(xiàn)城市下層人民的生活之艱辛和各類階級(jí)之間尖銳的矛盾沖突。兩種生存背景下的作家的心理體驗(yàn)自然大不相同,作家所面對(duì)的客觀世界和主管世界的沖突融合便是切身的心理體驗(yàn)。
四、總結(jié)
20世紀(jì)的中國(guó)飽受災(zāi)難,有良知的現(xiàn)代作家的主觀與客觀,即“內(nèi)心深處的激情”與“外界的事實(shí)”不合拍、不統(tǒng)一就勢(shì)必難免。于是就有了這些作家深重的“不安”和“內(nèi)心痛苦”的狀態(tài),這構(gòu)成了他們創(chuàng)作時(shí)的心理沖突。現(xiàn)代作家的文學(xué)寫(xiě)作,實(shí)際上便演變成心理上深刻而朦朧的搏斗史。正是因?yàn)槲谋緦?xiě)作與實(shí)際的心靈沖突形成了一種聯(lián)系緊密的“互文本性”,才使得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背后深藏了更多需要探知的心理奧秘。“痛苦的靈魂常常成就不凡的杰作。”在20世紀(jì)前半期那個(gè)特殊年代,一批現(xiàn)代作家經(jīng)歷著靈與肉的苦痛與掙扎,心理沖突推動(dòng)了他們的創(chuàng)作,而寫(xiě)作的字里行間又無(wú)不滲透出他們靈魂搏斗的痕跡。從心靈與寫(xiě)作這種互文本的參照出發(fā),有助于窺見(jiàn)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作家創(chuàng)作的諸多奧秘。對(duì)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作家心理沖突的思考是關(guān)注作家生命形態(tài)的研究視角,有助于有助于揭示出文學(xué)背后深藏的諸多心理奧秘。
參考文獻(xiàn):
[1]金莉莉.略論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作家的創(chuàng)作心理沖突[J].中國(guó)政法大學(xué)學(xué)報(bào),2012(4).
[2]吳浪平.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作家批評(píng)與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意識(shí)[D].華東師范大學(xué)博士學(xué)位論文,2012(4).
[3]發(fā),賈振勇.審美闡釋的理論期待視野──關(guān)于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評(píng)價(jià)標(biāo)準(zhǔn)的思考[J].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研究叢刊,2001(2).
[4]趙園.大革命后小說(shuō)關(guān)于知識(shí)者“個(gè)人與革命”關(guān)系的思考及“新人”形象的降生――兼談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中有關(guān)“戀愛(ài)和革命的沖突”的描寫(xiě)[J].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研究叢刊,2008(2).
篇(6)
回顧近二三十年來(lái),伴隨著鄉(xiāng)土題材影視作品中農(nóng)村敘事的變遷,可以窺見(jiàn)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的現(xiàn)代化與城市化進(jìn)程,但這種變遷,卻經(jīng)常與當(dāng)下中國(guó)農(nóng)村的現(xiàn)實(shí)迥然不同。從文化層面來(lái)說(shuō),現(xiàn)代化進(jìn)程尚未完成的中國(guó)仍是一個(gè)鄉(xiāng)土中國(guó),但當(dāng)城市化的浪潮淹沒(méi)了大部分的人,由此也掀開(kāi)了城市中心主義敘事的濫觴。流行文化中,幾乎每一個(gè)畫(huà)面都在精心地刻畫(huà)著城市的妖媚,而中國(guó)廣袤的農(nóng)村,則徹底被遮蔽、被邊緣化,成為“每個(gè)人的故鄉(xiāng)都在淪陷”的一道道憂傷。 作為歷史與傳統(tǒng)的鄉(xiāng)村
上世紀(jì)八九十年代,隨著尋根文學(xué)與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興起,從莫言、實(shí)、賈平凹、王安憶、路遙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中,能讀出濃郁的鄉(xiāng)土味,這些龐大的作者群,源源不斷地輸送著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作品,誕生了《白鹿原》、《爸爸爸》、《小鮑莊》、《紅高粱》、《綠化樹(shù)》、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馬橋詞典》、《檀香刑》、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受活》、《活著》等優(yōu)秀作品,帶來(lái)那個(gè)時(shí)代的文化盛宴。從《白鹿原》、《紅高粱》等作品中可以看到,莫言、實(shí)等作為依托于中國(guó)本土經(jīng)驗(yàn)的作家,以自身的鄉(xiāng)土生活經(jīng)驗(yàn)寫(xiě)就了反映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秩序的巨變。
此后20年內(nèi),大批以此作為藍(lán)本與劇本的影視作品,也集體作戰(zhàn)式地占領(lǐng)了電影與電視屏幕,其中電影作品的佼佼者包括《芙蓉鎮(zhèn)》(1986)、《黃土地》(1984)、《紅高粱》 (1987)、《孩子王》(1987)、《秋菊打官司》(1992)、《活著》(1994)、《九香》(1994)、《二嫫》(1994)、《草房子》(1998)、《一個(gè)都不能少》(1999)、《我的父親母親》(1999)、《那山那人那狗》(1999)等。這些作品同時(shí)也是中國(guó)“第五代”導(dǎo)演崛起的見(jiàn)證。
在電視上與《渴望》、《編輯部的故事》、《便衣警察》等都市生活劇分庭抗禮的是《籬笆·女人和狗》(1989)、《轆轤·女人和井》(1991)、《古船·女人和網(wǎng)》(1993)農(nóng)村三部曲等,產(chǎn)生了廣泛的影響。這3部電視劇以農(nóng)村家庭在時(shí)代背景下變遷與思想觀念的革新為主題,著重描述了農(nóng)村人心的變化和道德傳統(tǒng)的波動(dòng),構(gòu)筑了一個(gè)時(shí)代變異潮流中最真切的農(nóng)村景象。總的來(lái)說(shuō),那個(gè)時(shí)期的鄉(xiāng)土影視作品,由于創(chuàng)作者有著切身的鄉(xiāng)村生活的體驗(yàn)與觀察,而且深受中國(guó)鄉(xiāng)土農(nóng)耕文明影響,文化關(guān)懷上就顯得尤為充分。另外不得不提在尋根文學(xué)影響下,有關(guān)“”時(shí)上山下鄉(xiāng)知青題材的作品也反響巨大。根據(jù)葉辛同名小說(shuō)改編的反映知青生活的連續(xù)劇《蹉跎歲月》,雖只有短短4集,在1982年播出時(shí)引發(fā)全國(guó)對(duì)知青生活的回顧熱潮。主題曲《一支難忘的歌》唱紅大江南北。在這個(gè)期間,此類題材的影視作品也時(shí)有問(wèn)世。1995年播出了葉辛的另一部小說(shuō)《孽債》改編的20集同名連續(xù)劇,所描述的返城知青及其子女從遙遠(yuǎn)的西雙版納到上海尋親的故事,再次引起轟動(dòng)。
這一時(shí)期的影視作品注重內(nèi)在的思想性,反映了時(shí)代烙印以及農(nóng)村的苦難與變遷,以及通過(guò)農(nóng)村這個(gè)最具中國(guó)意義(承載著最多的傳統(tǒng)與苦難)的場(chǎng)域來(lái)反思民族性和國(guó)民性等,充滿批判與反思色彩,也一定程度上實(shí)現(xiàn)了一種文化的啟蒙,這都為這些作品增添了重量與價(jià)值,因此大部分在今日依然是經(jīng)典。
但隨著改革開(kāi)放的進(jìn)一步發(fā)展,特別是1990年代中后期,都市生活類作品越來(lái)越成為影視劇市場(chǎng)的主體,港臺(tái)生活劇和古裝劇一度興旺,吸引了大量的觀眾。鄉(xiāng)土題材的作品漸漸失去了優(yōu)勢(shì),創(chuàng)作數(shù)量減少尤其是有影響作品稀缺,使得農(nóng)村題材創(chuàng)作相比進(jìn)入低潮期。而且就算有些好的作品,“農(nóng)村”也只是作為一種鋪陳的背景或前奏了,比如《外來(lái)妹》(1991)、《情滿珠江》(1994)。這種重心的轉(zhuǎn)移,或許與創(chuàng)作者的新力量成長(zhǎng)也有莫大的關(guān)聯(lián)。在“第五代”導(dǎo)演由于各種原因紛紛轉(zhuǎn)型拍商業(yè)片時(shí),“第六代” 導(dǎo)演逐漸嶄露頭角。這一批1980年代中后期進(jìn)入北京電影學(xué)院導(dǎo)演系、1990年代后開(kāi)始執(zhí)導(dǎo)電影的一批年輕導(dǎo)演,產(chǎn)生了《北京雜種》、《媽媽》(張?jiān)ⅰ抖旱娜兆印贰?《十七歲的單車》 (王小帥)、《長(zhǎng)大成人》(路學(xué)長(zhǎng))、 《巫山云雨》(章明)、 《頭發(fā)亂了》(管虎)、 《郵差》(何建軍)、 《頤和園》、《蘇州河》(婁燁)、《愛(ài)情麻辣燙》、《洗澡》(張揚(yáng))、 《小武》、 《站臺(tái)》(賈樟柯)、《月蝕》(王全安)、《可可西里》(陸川)、《瘋狂的石頭》、 《無(wú)人區(qū)》(寧浩)等佳作。但從題材上一個(gè)明顯的區(qū)別是,“第六代”導(dǎo)演的關(guān)注重心已經(jīng)從鄉(xiāng)土農(nóng)村轉(zhuǎn)移到小城鎮(zhèn)以及城市生活。 作為“他者”的鄉(xiāng)村
進(jìn)入新世紀(jì),鄉(xiāng)土題材的影視作品就開(kāi)始式微,《劉老根》(2002)及其系列可算是為數(shù)不多的在收視率與關(guān)注度上都相對(duì)不錯(cuò)的作品。在2000年到2010年這10年中,還有《插樹(shù)嶺》、《馬大帥》、《都市外鄉(xiāng)人》、《別不拿豆包當(dāng)干糧》、《希望的田野》、《民工》、《正月里來(lái)是新春》、《燒鍋屯鐘聲》、《當(dāng)家的女人》、《鄉(xiāng)村愛(ài)情》、《圣水湖畔》、《種啥得啥》、《清凌凌的水藍(lán)瑩瑩的天》、《母親是條河》等有關(guān)農(nóng)村的影視作品,但絕大多數(shù)都難以重現(xiàn)上世紀(jì)八九十年代的那種收視率與口碑反應(yīng)。它們講述的幾乎都是東北農(nóng)村的故事,具有強(qiáng)烈的地域性。
在電影上,有《25個(gè)孩子一個(gè)爹》、《天上的戀人》、《暖春》、《青紅》、《圖雅的婚事》、《天狗》等作品,但像《盲井》、《盲山》這樣令人眼前一亮的優(yōu)秀作品并不多見(jiàn)。《上車,走吧》、《高興》、《民工》、《馬大帥》、《都市外鄉(xiāng)人》等作品講述的都是農(nóng)村人融入城市的過(guò)程,明顯的是,這些影視作品,在還原真實(shí)狀態(tài)的農(nóng)村,比如污染、災(zāi)害、農(nóng)民上訪、留守兒童、空巢、基層干部貪污等等廣泛存在的現(xiàn)實(shí)問(wèn)題上基本呈現(xiàn)缺失或無(wú)力的狀態(tài),一種與現(xiàn)實(shí)的犬儒主義彌漫在影視作品的深處,去苦難化、喜劇化、唯美化成為通行的手法。
以最近持續(xù)熱播的電視劇《鄉(xiāng)村愛(ài)情變奏曲》和《櫻桃紅》為例,鄉(xiāng)村敘事的失真,以及反思性和現(xiàn)實(shí)關(guān)照性的消失可見(jiàn)一斑。一個(gè)例子是,在它們的敘事里,鄉(xiāng)鎮(zhèn)和村干部清一色是正面人物,體現(xiàn)出一貫的“批評(píng)到鄉(xiāng)長(zhǎng)為止”的犬儒主義底色。劇中的社會(huì)狀況,最終的落腳點(diǎn)也都如同劇作者趙本山的小品一樣,歸結(jié)為“現(xiàn)在農(nóng)民生活都富裕了,有錢(qián)了”、“政府的政策好了,農(nóng)民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”的皆大歡喜。與上世紀(jì)八九十年代的鄉(xiāng)土電視劇比,沒(méi)有任何的思想性,充其量只是個(gè)農(nóng)村版肥皂劇。而且正如論者曾念長(zhǎng)指出的,在《鄉(xiāng)村愛(ài)情》中,“盡管象牙山村依然是一個(gè)親戚里道的熟人社會(huì),但我們已經(jīng)看不到傳統(tǒng)農(nóng)村社會(huì)的生活鏡像。一座散發(fā)著商業(yè)美學(xué)光澤的溫泉度假山莊,是城市休閑消費(fèi)漫延到農(nóng)村的產(chǎn)物;一片按照現(xiàn)代農(nóng)業(yè)技術(shù)標(biāo)準(zhǔn)化開(kāi)發(fā)出來(lái)的果林,是對(duì)商業(yè)時(shí)代新田園美學(xué)的謳歌;一家快速擴(kuò)建的豆奶制品廠,則是得益于上海企業(yè)的商業(yè)化支援;一臺(tái)反復(fù)植入廣告的品牌小轎車,顯示了來(lái)自上海的這家汽車公司對(duì)挺進(jìn)農(nóng)村市場(chǎng)的勃勃野心”。“鄉(xiāng)愛(ài)”系列外形上雖仍屬鄉(xiāng)土題材,實(shí)質(zhì)已經(jīng)變成了城市化擴(kuò)張的生動(dòng)寫(xiě)照。
而去年在央視播放的《知青》則遭遇了眾多的詬病,其沿襲了張藝謀《山楂樹(shù)之戀》的風(fēng)格,只將苦難作為一個(gè)若即若離與可有可無(wú)的背景,詩(shī)意成分被刻意放大,被耽誤的青春被塑造成青春無(wú)悔、苦難荒唐被描繪為純潔無(wú)暇、貧窮被當(dāng)作了樸素。這一點(diǎn)還可以充分地體現(xiàn)在《巴爾扎克與小裁縫》、《美人草》、《血色浪漫》、《與青春有關(guān)的日子》、《北風(fēng)那個(gè)吹》等劇中。隨著時(shí)間的發(fā)展,“”早已漸漸成為年輕一代的記憶空白,于是,“”及其上山下鄉(xiāng)開(kāi)始發(fā)生了種種去政治化和唯美化,這種圍繞著青年人的劇目,呈現(xiàn)出玩世不恭或感傷主義的情調(diào),無(wú)意間淪為美化歷史的化妝術(shù),迎合當(dāng)下“小資”文化需求。新世紀(jì)“知青”題材中,農(nóng)村敘事被嵌入大量懷舊色彩,歷史的傷痕被以曖昧的形式加以包裝,被美化的鄉(xiāng)村生活成為故事的蕾絲花邊,仿佛那個(gè)時(shí)代的荒誕與人性壓抑,都成為一種美好的象征。于是,“知青”背后的農(nóng)村中國(guó),實(shí)際上已經(jīng)成為中國(guó)當(dāng)代史上極具特殊寓意表征的一個(gè)時(shí)代印記和文化符號(hào),在不同的年代,不停地被翻新出新的社會(huì)價(jià)值,或者榨出新的象征意義,但這片土地發(fā)生過(guò)的或正在發(fā)生的困難卻被刻意遺忘。人們選擇性地遺忘,將這一段歲月有意無(wú)意地消抹掉,或者移花接木,使用歷史的化妝術(shù),將之唯美化。而每每看到這樣的泛濫抒情時(shí),筆者腦海總浮現(xiàn)出電影《天浴》里的骯臟與殘酷,還有更甚于《一九四二》的餓殍遍地。
以去年上映的顧長(zhǎng)衛(wèi)作品《最愛(ài)》為例,其原著是閻連科的《丁莊夢(mèng)》,小說(shuō)描繪河南農(nóng)村中真實(shí)存在的艾滋病籠罩下的荒唐與災(zāi)難。有評(píng)論家認(rèn)為《丁莊夢(mèng)》風(fēng)格冷峻、辛辣,觸目驚心地展示了深藏于農(nóng)民性格深處形形的愚昧、頑劣、悲壯和辛酸。艾滋病的魔鬼籠罩著,人們卻被固有的劣根性所左右,不顧其他,因此將其稱為“中國(guó)版的《鼠疫》和《大疫年紀(jì)事》”。但對(duì)比原著,電影在被審核剪輯之后,原著的重量明顯退減而顯得“輕飄飄”,電影更像是艾滋病的公益宣傳片,缺少了原有的震撼力與現(xiàn)實(shí)反思性。電影啟用了章子怡、郭富城、濮存昕、蔡國(guó)慶等“大腕”,愛(ài)情偶像劇的模板呼之欲出。而本來(lái)真實(shí)的鄉(xiāng)村里的殘酷,淡化成一個(gè)烘托凄美愛(ài)情的背景,反思性與深刻性被大大弱化。
篇(7)
摘要賈平凹是中國(guó)當(dāng)代文壇一位獨(dú)樹(shù)一幟的作家,縱觀他30多年的創(chuàng)作,濃厚的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成為貫穿其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的一條重要的精神線索,從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到地域文化到風(fēng)土人情;從現(xiàn)代文明的沖擊和無(wú)奈地離鄉(xiāng)返鄉(xiāng),多種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構(gòu)成了賈平凹小說(shuō)獨(dú)特的鄉(xiāng)土人文藝術(shù)。本文從商州情結(jié)、女性情結(jié)和離鄉(xiāng)返鄉(xiāng)情結(jié)三個(gè)方面,淺談了賈平凹小說(shuō)創(chuàng)作中的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的具體表現(xiàn)。
關(guān)鍵詞:賈平凹 小說(shuō)創(chuàng)作 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
中圖分類號(hào):I206.7文獻(xiàn)標(biāo)識(shí)碼:A
一 賈平凹的小說(shuō)創(chuàng)作和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
賈平凹是中國(guó)當(dāng)代文壇中屈指可數(shù)的文學(xué)大家,也是一位最具叛逆性和創(chuàng)作精神的作家。自1973年開(kāi)始發(fā)表作品以來(lái),其目前已出版的作品版本達(dá)到300多種。上個(gè)世紀(jì)70年代末,賈平凹初登文壇,那時(shí)的青年文學(xué)愛(ài)好者可謂是風(fēng)華正茂,書(shū)生意氣,作品內(nèi)容以反映社會(huì)變革和生活變化為主。如《水》、《清河上的婚事》、《竹子和含羞草》等。1978年,賈平凹憑借小說(shuō)《滿月兒》,獲得全國(guó)優(yōu)秀短篇小說(shuō)獎(jiǎng),他也因此在中國(guó)文壇上嶄露頭角。1983年,他創(chuàng)作了小說(shuō)《商州初錄》,標(biāo)志著他的小說(shuō)創(chuàng)作邁上了一個(gè)新的臺(tái)階,此后的商州系列,在中國(guó)文壇上掀起了一場(chǎng)尋根文學(xué)的熱潮。1984年,賈平凹的《雞窩洼的人家》和《臘月正月》等幾部小說(shuō),把農(nóng)村經(jīng)濟(jì)體制改革下的商州展示給了全國(guó)人民,也堅(jiān)定了他在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創(chuàng)作道路上的行走。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,他的作品呈現(xiàn)出強(qiáng)烈的神秘文化色彩,源于他對(duì)人生、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和關(guān)注,如《天狗》、《人極》、《煙》等,表達(dá)出對(duì)生命的玄思。進(jìn)入90年代,中國(guó)城鄉(xiāng)之間的差距越來(lái)越大,農(nóng)村發(fā)展和農(nóng)村文化引起了賈平凹這位鄉(xiāng)土作家的深切關(guān)注。1993年,他創(chuàng)作了《白夜》,刻畫(huà)了一個(gè)農(nóng)村人進(jìn)城尋找精神家園的尋夢(mèng)過(guò)程,表達(dá)出城市和農(nóng)村之間的對(duì)立。隨后的《土門(mén)》,表現(xiàn)了在城市文明的發(fā)展下,農(nóng)村文明的堅(jiān)守和退讓,直至最后消失的過(guò)程。2005年創(chuàng)作的《秦腔》,更是一舉拿下了茅盾文學(xué)獎(jiǎng),成為新世紀(jì)中國(guó)文壇的抗鼎巨作。最新的作品《高興》,還是沒(méi)有離開(kāi)農(nóng)村、沒(méi)有離開(kāi)鄉(xiāng)土,雖然主人公在變化,故事情節(jié)在變化,但是不變的卻是賈平凹這位農(nóng)村漢子對(duì)生育他、養(yǎng)育他的這片鄉(xiāng)土的摯愛(ài),對(duì)這片鄉(xiāng)土上人們的關(guān)注和同情,以及他在文學(xué)藝術(shù)上的不斷追求。
所謂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,就是依靠作家的回憶來(lái)描寫(xiě)農(nóng)村生活,帶有濃厚的鄉(xiāng)土氣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說(shuō)。賈平凹正是以自己的故土商州為最主要的創(chuàng)作背景,并把農(nóng)民作為自己關(guān)注的表現(xiàn)的對(duì)象,進(jìn)而給了我們以極大原生態(tài)的鄉(xiāng)土美的感受。
二 賈平凹小說(shuō)中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濃重的原因簡(jiǎn)析
1 源于他對(duì)鄉(xiāng)土的深切眷戀
賈平凹1953年出生于陜西省的丹鳳縣金盆鄉(xiāng)。這個(gè)青山連綿、山清水秀的小山村,因地理位置的原因,自古就是秦楚文化的交匯地帶。它既有西北關(guān)外的豪放和雄渾,也有江南水鄉(xiāng)的婉約和靈秀。這塊肥沃美麗的山水養(yǎng)育了賈平凹,這里的文化積淀成為了他從事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最初的源泉,當(dāng)這位游子把對(duì)故土的情感在他的文字中予以痛快淋漓的宣泄時(shí),我們能夠感受到這種情感的真切。也正是故土的一花一草、一人一物,為賈平凹的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,并使他將現(xiàn)實(shí)中貧瘠偏遠(yuǎn)的故鄉(xiāng)以美好的詞語(yǔ)予以描繪,展示了山村里優(yōu)美的自然風(fēng)光和山村人的勤勞和樸實(shí)。而這一切都是源于他對(duì)故鄉(xiāng)深切眷戀的本能意識(shí)。
2 實(shí)實(shí)在在的農(nóng)村人
賈平凹出生于山村,祖上幾輩人都是地地道道的農(nóng)民,而他對(duì)此也從不諱言,甚至還主動(dòng)提出過(guò)自己身上具有農(nóng)民身上的“丑陋、卑下、委瑣”等缺點(diǎn),對(duì)于這個(gè)身份,賈平凹是又愛(ài)又恨的:愛(ài)是因?yàn)檗r(nóng)村生活中那些幸福或者痛苦的經(jīng)歷,是他生命中具有永恒價(jià)值的財(cái)富;恨的是,從小的是是非非、災(zāi)災(zāi)難難的生活,讓他受到了冷漠和歧視,形成了自卑、憂郁的性格,這對(duì)于他日后的創(chuàng)作影響十分巨大,以至于他在創(chuàng)作中,只有將故鄉(xiāng)的景物作為描述的對(duì)象,才能獲得心靈上的安寧和慰藉。這種農(nóng)村人的生活經(jīng)歷和因此而形成的個(gè)性特征,也是他的作品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濃重的重要原因。
3 “城里農(nóng)村人”的特殊身份
賈平凹是在農(nóng)村長(zhǎng)大的,雖然后來(lái)通過(guò)上大學(xué)得以留在了城中,但是無(wú)論走到哪里,他的身上都始終帶著農(nóng)村人的烙印。面對(duì)著琳瑯滿目、光怪陸離的大城市,他開(kāi)始變得不知所措,開(kāi)始懷念以前的鄉(xiāng)村生活。一方面,他是見(jiàn)過(guò)城里大世面的城市人;一方面他又是不能融于城市生活的鄉(xiāng)下人,對(duì)此他產(chǎn)生了強(qiáng)烈的自卑感,要以文學(xué)成就來(lái)證明自己,給自己以安全感,更要在作品中描繪出一個(gè)自己真正喜歡的農(nóng)村世界,于是商州就成了他的建筑作品之一,他把自己創(chuàng)作的根扎在商州這塊古老的土地上,從鄉(xiāng)土文明中挖掘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,讓城中的自己和鄉(xiāng)下的自己進(jìn)行著最本質(zhì)的交流和呼應(yīng)。
三 賈平凹小說(shuō)創(chuàng)作中的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
1 商州情結(jié)
商州是賈平凹的故鄉(xiāng),是他小說(shuō)創(chuàng)作的源泉。商州是今天的商洛地區(qū)。陜西省依據(jù)歷史傳統(tǒng)可以分為三大塊,即陜北、關(guān)中和陜南,而商州則位于關(guān)中和陜南之間的秦嶺南麓。秦嶺是我國(guó)南方和北方的自然分界線,所以無(wú)論是商州的氣候、物象、山川等,都呈現(xiàn)出明顯的過(guò)渡性特征,并先后產(chǎn)生過(guò)漢唐文化、秦文化和楚文化,而這些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經(jīng)過(guò)幾千年的傳揚(yáng),逐漸滲透到了商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,震天響的秦腔、中堂上惟妙惟肖的老虎、大門(mén)上公正的對(duì)聯(lián),都是商州人民智慧的象征。賈平凹有一部專門(mén)以商州為描寫(xiě)對(duì)象的作品集《商州初錄》,在談及這部作品時(shí),他曾經(jīng)表示:
“過(guò)去商州市什么樣子,這么多年來(lái)又是什么樣子,而現(xiàn)在又是什么樣子,這已經(jīng)成了急需向外面世界披露的問(wèn)題,也是我寫(xiě)這幾部小說(shuō)的目的。”
在他的筆下,商州風(fēng)景優(yōu)美,人民勤勞聰明,既有西北的雄渾,又有江南的婉約,儼然是一方人間的圣地。這種對(duì)商州的極力頌揚(yáng),正是出于他對(duì)商州這片土地的深切熱愛(ài),這片養(yǎng)育他的土地,已經(jīng)深深地將烙印留在了賈平凹的心中,他的商州系列小說(shuō)中形形的人物正是現(xiàn)實(shí)中人物的真實(shí)寫(xiě)照,那些獨(dú)特的民俗風(fēng)情和歷史、神話、傳說(shuō)又成為他源源不斷的藝術(shù)源泉。在他看來(lái),商州已經(jīng)不再是行政區(qū)劃中的商州了,而是滲透了他強(qiáng)烈的個(gè)人精神的理想化的商州,成為了他永遠(yuǎn)留戀和向往的精神家園,這里記錄了他的成長(zhǎng),見(jiàn)證了他的成功。現(xiàn)在,他要用自己的作品,來(lái)回報(bào)這片給予他太多太多的土地。
2 鄉(xiāng)土女性情結(jié)
在賈平凹的作品中,塑造了大量的西北女性的形象,傾注了他對(duì)于鄉(xiāng)土女性獨(dú)特的關(guān)注和認(rèn)識(shí)。在他的筆下,每一個(gè)女子都是鮮活的、敢愛(ài)敢恨的,她們有的俊俏、有的溫柔、有的多情、有的嫻熟,而且都有著自己篤定的想法和追求,對(duì)自己的追求永遠(yuǎn)都不放棄。賈平凹把西北女子那種善良、率真、潑辣的特征體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,在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背后,則是他對(duì)愛(ài)情、倫理道德、人生的精神關(guān)照。如《浮躁》的主人公小水,這是一個(gè)溫柔如水,但內(nèi)心剛烈的鄉(xiāng)村女子,她深深地愛(ài)著金狗,但是在傳統(tǒng)觀念的束縛下,她不能與具有較強(qiáng)現(xiàn)代意識(shí)的英英相抗衡,因?yàn)樗幌裼⒂⒁粯荧I(xiàn)出了自己的。但她卻沒(méi)有責(zé)怪金狗和英英,反而是真切地祝福他們。后來(lái)金狗落難,她始終不離不棄,支持他開(kāi)始新的生活。自始至終,無(wú)論遇到什么樣的困難,小水都沒(méi)有退縮,沒(méi)有屈服于命運(yùn),而是始終對(duì)生活充滿了熱情。隨著時(shí)代的變遷,賈平凹小說(shuō)中的女主人公們也開(kāi)始有了內(nèi)涵上的新的發(fā)展,如《雞窩外的人家》中的小月不再有傳統(tǒng)女性的羞澀和保守,而是有了變革時(shí)代浮躁的氣息;《臘月正月》里的小月改變了傳統(tǒng)的擇偶觀念,自主地選擇了理想中的婚姻和愛(ài)情。這些都是西北鄉(xiāng)土女性傳統(tǒng)美德和現(xiàn)代精神的完美展現(xiàn)。當(dāng)然,隨著時(shí)代的進(jìn)步和社會(huì)的發(fā)展,鄉(xiāng)土女性的思想觀和價(jià)值觀也發(fā)生了嬗變,賈平凹也敏銳地觀察到了這一點(diǎn),并在其作品中的女性身上體現(xiàn)出鮮明的經(jīng)濟(jì)時(shí)代的特征。他借助于對(duì)這些女子形象的塑造,抒發(fā)了自己對(duì)于社會(huì)和人生的看法。如《廢都》之中的農(nóng)村小保姆柳月,她渴望走出農(nóng)村,做一個(gè)城里人,但是她沒(méi)有知識(shí)和能力,只能做一些保姆類的服務(wù)性工作,因?yàn)橛幸环N強(qiáng)烈的危機(jī)意識(shí)和功利意識(shí),所以她開(kāi)始利用自己的身體,通過(guò)吸引男人來(lái)改善自己的生活,甚至幻想著有一天能成為莊之蝶的主婦。她后來(lái)嫁給了市長(zhǎng)的有殘疾的兒子,因?yàn)樗溃松眢w和姿色,她實(shí)在是一無(wú)所有。在她的身上,反映出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下農(nóng)村女性人生觀和價(jià)值觀的深刻變化。從上述的幾個(gè)例子可以看出,無(wú)論是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好女人,還是追逐現(xiàn)實(shí)物質(zhì)利益的“壞”女人,我們都能感受到賈平凹是在用心描寫(xiě)鄉(xiāng)土的女性,而這也成為他小說(shuō)創(chuàng)作中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的重要表現(xiàn)。
3 離鄉(xiāng)―返鄉(xiāng)情結(jié)
賈平凹19歲離開(kāi)故鄉(xiāng),但他的心卻一直都沒(méi)有離開(kāi)過(guò)故鄉(xiāng),而在作品中體現(xiàn)還鄉(xiāng)是他補(bǔ)償故土最好的生命情結(jié)。在他的作品中,我們經(jīng)常可以看到主人公離鄉(xiāng)―返鄉(xiāng)的情節(jié),這些都傳達(dá)出他作為一個(gè)鄉(xiāng)土知識(shí)分子的現(xiàn)代性體驗(yàn)和面對(duì)現(xiàn)代化負(fù)面影響的無(wú)奈和糾結(jié)。在他早期的作品中,主人公都是一些農(nóng)村青年,他們因不滿足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(nóng)耕生活,而渴望走出山村,去了解外面的世界,追求新的生活。《雞窩洼的人家》中的禾禾本來(lái)有著一個(gè)幸福美滿的家庭,一家三口,日子雖然不是太富裕,卻也其樂(lè)融融,但是禾禾不滿足生活的現(xiàn)狀,早已被城里傳來(lái)的致富信息所吸引,開(kāi)始放棄經(jīng)營(yíng)土地、做豆腐、打狐貍,幾經(jīng)折騰,不但沒(méi)有賺到錢(qián),反而落得個(gè)妻離子散。但是這都沒(méi)有阻擋他的腳步,他去城里考察,學(xué)習(xí)別人的經(jīng)驗(yàn),終于在養(yǎng)蠶上獲得了成功,經(jīng)濟(jì)上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在賈平凹看來(lái),山村青年是應(yīng)該走出去并在外面學(xué)得經(jīng)驗(yàn)和技術(shù),來(lái)改善自己原本窮困落后的生活,繼而帶動(dòng)整個(gè)鄉(xiāng)村的發(fā)展,這也是他在創(chuàng)作之初對(duì)于離鄉(xiāng)的看法和認(rèn)識(shí)。但是隨著社會(huì)的發(fā)展,他的價(jià)值取向也發(fā)生了變化。《浮躁》中的金狗,復(fù)員回家后并沒(méi)有在農(nóng)村里安分地種田務(wù)農(nóng),而是要到城里大展宏圖,并且當(dāng)上了一名記者,而當(dāng)他面對(duì)著一個(gè)個(gè)虛假新聞和虛假報(bào)道時(shí),金狗開(kāi)始迷惑了,這與他心目中理想的城市狀態(tài)是截然相反的,一個(gè)農(nóng)村出身的正直青年的本性讓他決心揭發(fā)這些虛假丑惡的現(xiàn)象,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權(quán)貴,最終換來(lái)了牢獄之災(zāi)。出獄后,他發(fā)現(xiàn)還是自己的家鄉(xiāng)最純凈、最美好,于是毅然返回了家鄉(xiāng)。賈平凹近作《高興》中的劉哈娃,在老家不惜賣腎蓋房娶媳婦兒,卻仍然沒(méi)能如愿,于是決心進(jìn)城尋找自己理想的生活。他認(rèn)為自己的一只腎賣給了西安人,自己就是西安人了,他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劉高興,想要做一個(gè)真正的城里人,和他的同鄉(xiāng)五福一起撿破爛。但最后他不但沒(méi)有掙到錢(qián),五福還搭上了性命,而他則堅(jiān)持要把五福的尸體背回家,認(rèn)為老家才是他們最好的歸宿。進(jìn)城圓城里人夢(mèng)的農(nóng)民為什么如此艱難?是什么讓他們不愿意回到家鄉(xiāng)?是家鄉(xiāng)的貧窮讓他們被逼無(wú)奈,還是物質(zhì)精神的過(guò)分刺激讓他們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?賈平凹對(duì)此都進(jìn)行了深刻的思索,不光寫(xiě)到了他們的物質(zhì)生活,也寫(xiě)了他們的精神生活,反映出了他強(qiáng)烈的憂患意識(shí)。
除了上述的商州情結(jié)、女性情結(jié)、離鄉(xiāng)―返鄉(xiāng)情結(jié)外,賈平凹的小說(shuō)中還表現(xiàn)出民俗情結(jié)、土語(yǔ)情結(jié)等。他帶著對(duì)故土的眷戀和崇拜,把這里的山水、人物、語(yǔ)言、民俗,用真誠(chéng)的語(yǔ)言和質(zhì)樸的故事展現(xiàn)給我們。閱讀賈平凹帶給我們清泉般的鄉(xiāng)土作品,讓我們對(duì)鄉(xiāng)村有了一個(gè)全新的認(rèn)識(shí),鄉(xiāng)土不再是“土”,不再是“俗”,而是和高雅藝術(shù)一樣,都是對(duì)日常生活的真實(shí)寫(xiě)照。雖然高度發(fā)達(dá)的現(xiàn)代文明和鄉(xiāng)土中的古老文明有一些格格不入,但賈平凹并沒(méi)有予以回避,而是在努力地尋找著一個(gè)契合點(diǎn),他既深情守望著這片未被污染的故土,又希望它能夠在現(xiàn)代文明的沖擊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。賈平凹用真情感動(dòng)著故土的每一寸土地,以及與他同樣熱愛(ài)這片土地的人民。
參考文獻(xiàn):
[1] 賈平凹:《商州三錄》,陜西旅游出版社,2001年版。
[2] 賈平凹:《賈平凹散文自選集》,漓江出版社,1990年版。